板块导航
For Discuz! X2.5 © hgcad.com
比如,和人类一样免受折磨的权利,换句话说,动物应该被当作人同等看待,而不仅仅被当作人类的财产或工具,无论在法律层面或是精神层面。
立法动物权利
在一些国家,已经立法保障动物权利。1992年,瑞士法律上确认动物为“生物”(beings),而非“物品”(things); [1] 2002年,德国将动物保护的条款写入宪法。 [2] 由澳洲学者彼得·辛格(Peter Singer) 建立,基地位于美国西雅图的“泛类人猿计划”,目前正在争取美国政府采纳其所提出的《泛人猿宣言》,这份宣言呼吁赋予一个由大猩猩、猩猩以及两个亚种的黑猩猩组成的“平等群落”以三项基本权利:生存权、个体自由权和免受折磨权。 [3]
评判者认为
而批评者认为,由于动物无法对社会契约进行讨论或是做出道德判断,不能够顾及他人的权利,甚至根本对权利没有概念,因此不能被认为享有精神上的权利。动物权利主义学者Roger Scruton认为这些人的逻辑是“因为只有人类担负责任,所以也只应由人类享有权利”。
一些动物权利主义的批评者认为,尽管从根本上来说,将动物用于食用、娱乐或科学研究没有什么错,但仍应立法保障这些动物免受不必要的痛苦。这种观点被称为“动物福利主义”,也是某些老牌动物保护组织所持的观点,这些组织中包括英国皇家预防虐畜协会。
主要观点
动物权利的观点包括:
所有(或者至少某些)动物应当享有支配自己生活的权利;动物应当享有一定的精神上的权利;动物的基本权利应当受法律保障;这些观点反对将动物当作一般财货或是为人类效力的工具,常常与“动物福利”主义相混淆,动物福利主义仅仅关心动物不受虐待,而不试图保障动物精神上的权利。 [4]
权利区分
动物权利主义者并不主张动物与人类享有完全同等的权利,比方说,他们不认为家禽应该享有选举权。
一些动物权利主义者认为拥有感知力(能够自知)的动物与其他更原始的动物应该被区别对待:只有拥有感知能力(或较强烈自我意识)的动物才享有对自己生命及肉体的支配权,而不考虑人类把它们看作什么用途。
另一些动物权利主义者将这种权利推广到所有动物身上,包括那些没有自我意识甚至没有进化出神经系统的动物。他们坚持认为,人类及其一些机构为了食用、娱乐、制作化妆品、制衣、进行科学实验等等目的,将动物商品化的行为,违背了动物支配生命的基本权利。
多数人认可大型猿类拥有高度智慧,能够判断自身处境以及行为动机,当自由受到限制时,它们会感到沮丧。
相比之下,许多其他动物只拥有非常简单的神经系统,比如水母,只比一只机械手复杂一点,只能进行简单的应激反应,既无法中止也无法计划自己的行为,当然也不能判别自己是否自由。从生物学上的定义来看,水母毫无疑问属于动物,但从动物权利的观点来看,水母是否应被划归“蔬菜类”也未可知。就如何判定一个有机体是否属于应享有权利的“动物”,目前还没有一个被普遍认可的标准。
因此,关于动物权利的争论(与堕胎权的争论很像)就因难以确定一个简单、一刀切的判别标准而困难重重,这一标准,即使在生物学实践中也很难确定,当然,生物学中充满了复杂而多样的渐变性。按神经生物学的标准,水母、农场饲养的鸡、实验室的小白鼠以及家养的猫分别分布在一张复杂、多维度的坐标图中,坐标图的一端标着“近乎植物”,另一端标着“高度智慧”。
研究历史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的序言中,曾对动物权利的观念做了简述,他说人类从动物进化而来,而又不像其他动物那样“缺少智力和自由”,但是,其他动物也是有知觉的,“它们同样应该享有自然赋予的权利,人类有义务维护这一点”,他特别指出“动物有不被虐待的权利”。
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认为在本质上其他动物与人是一致的,尽管动物缺乏思考能力。尽管他为人类食用动物的行为做出了功利主义的辩解,他仍旧呼吁给予动物道德关怀
Tom Regan 在著作《动物权利状况》和《空空的牢笼》中,从另一个角度对此做出了解释。他将人类以外的动物看作“生命的载体”,赋有与人类同样的权利,尽管这种权利未必要与人类的在程度上完全一致。这意味着这些动物与生俱来具有与人同等的重要性,而不能仅仅被看作是一种用于达到目的的手段。
Gary Francione在《动物权利导言》等中著作指出,如果动物被当作财货,那么任何赋权于动物的行为都将直接被这种所有权状况损害。Francione将感知能力作为道德判断的唯一标准。他认为在美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动物权利运动,有的只是动物福利主义。在为罗格斯大学动物权利法项目所作的研究中,他指出任何不以解放动物奴隶状态的动物权利努力都是徒劳的,那只会导致剥削动物的制度化,这些做法在逻辑上自相矛盾,不能丝毫改善动物所处环境。Francione称一个一边把猫和狗当成宠物豢养、一边屠杀鸡、牛、猪来食用的社会为“道德分裂”。
各地法规[url=]编辑[/url]
尽管没有立法赋予动物权利,但法律对动物提供了保障。刑法对虐待动物进行惩罚;其他诸如在城市和农场饲养动物、动物的国际贸易以及动物免疫,都有专门的法规加以规范。这些法规使动物免受不必要的身体伤害,并对可以使用的动物种类加以界定。在英美法系国家,人们死后可以为动物设立专门的慈善基金,以使动物的生活得到保障。这些基金设立人的行为和愿望受到法律保护。
不少国家和地区均设有保护动物的组织,例如香港的爱护动物协会。
学术界比较认可的动物福利概念:动物福利通常被定义为一种康乐状态,在此状态下,至少动物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而痛苦被减至最小。
从此概念中可以看出,动物福利不涉及到是否宰杀或使用动物的问题,它的核心思想是满足动物的基本需要,减少动物不必要的痛苦。
事实上,许多应用动物福利研究者向来认为,死亡从来就不是最痛苦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许多身患痛苦疾患的病人为什么要主动寻求安乐死的原因。动物福利研究者认为,我们不是不可以使用动物,不是不能宰杀动物,最重要的是,在我们利用动物的过程中,不要给动物带来不必要的痛苦。这才是动物福利所倡导的。
动物的生理福利容易量化、直观,很容易被人们接受。例如在动物生产中,我们可以用无疾病或寄生虫作为动物具有良好健康的评价标准;无营养缺乏、保持良好体况作为饲养合理的衡量指标;而良好的圈舍条件则可以避免动物肢体损伤,使躯体感受舒适。在动物生产中,根据具体实际情况,尽可能地保障动物具有良好健康、制定合理的饲养工艺以及创造良好的圈舍条件,不仅仅能够提高动物福利水平,而且还能极大地提高生产水平。
容易引起大家争议的是动物的精神(心理)福利方面的内容。很多人对于动物是否具有主观感受和心理意识尚存争议,所以在评价动物福利时是否应该考虑动物的感觉(feeling)这一问题上很难达成共识。由于目前的科学手段很难准确测量出动物的心理状态,如焦躁(Agitation)、压抑(Depression)、痛苦(Distress),所以我们只能根据动物的行为进行主观判断。衡量动物福利,生产力被证实是不可靠的,而利用生理学与生物化学的方法也很难获得理想结果,因此,应该采用行为学研究方法对动物福利进行评价。
关于动物权利及其保护的必要性,从逻辑上讲,似乎有如下三种论证思路:第一,保护动物是为了更好地保护环境以及物种多样性,进而更好地保护人类;第二,保护动物是人的恻隐之心的必然要求,并且也有利于提升人类社会的道德水准;第三,保护动物就是为了保护动物本身,因为动物与人类一样,都为天地所化育因而也有同样的生存、发展之权利。
看上去,如上第一种思路似乎是最难成立的,因为这种思路骨子里的逻辑是:动物权利不过是保护人类的一种工具或途径而已,果真如此,则所谓“动物权利”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因为权利的基本属性正在于它的目的性、或者说非单纯工具性。相对应地,如上第三种思路则似乎是最应当被倡扬的,但实际上一旦将这种思路落实到实践中就立马会遇到这样的问题:首先,既然动物按其本性有其生存、发展的权利,那么,人类是否不应该或者说没有权利做任何干涉动物自然存续的事情?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是因为在大自然前面,人类历来就与其他动物构成了一种竞争的关系,而竞争就一定意味着一方对另一方的压制、乃至剥夺;换句话说,竞争、压制、限制、剥夺本就是一项根本的自然法则。因此,问题就变成了人类应当如何在干涉动物的自在状态时又尊重动物、保护动物?有一种听起来很美的说法,即人类应当按照动物的本性那样来对待动物。以动物保护法专家建议稿为例,其中就提到了这样一条,“不能让动物做一些它不能做到或者伤害动物的事情,如让狮子跳进火堆、钻火圈……”我之所以说这种思路听上去很美,是因为所谓“动物的本性”不是一个可以自动显现的东西,它必得仰赖人的“认定”,因此,所谓按照动物本性来对待动物,其实说白了也就是按照人类所认为的动物之本性对待动物;也因此,这第三种思路一旦落实起来,最终仍然不免掉入到“人类中心主义”的泥淖之中。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如上第二种思路又如何。显然,它也是有问题的,因为第一,如果仅仅将动物权利诉诸于不说虚无缥缈,至少也是不甚牢靠的人类恻隐之心,则无疑等于说动物权利没有其存在的坚实基础;第二,如果以一种较劲儿的态度看待此种观念,我们完全有理由问这样一个问题:有什么足够的证据可以表明,动物权利的保护有利于提升人类的道德水准?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问得更赤裸一点:动物权利主义者的道德水准就一定高于那些非动物权利主义者?第三,也许也是更根本的是,这第二种思路其实仍然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因为它根本上仍然把动物权利看做一种工具。
无论人们的出发点是什么,一旦开始尝试着将某种动物权利观念落到实处,就将不可避免地把动物对象化、客体化,进而也从根本上违背权利的非单纯工具性属性。仅此而言,我们也完全有理由怀疑,所谓“动物权利”的说法尽管有一定的道德吸引力,但却很可能是一个不严谨的说辞。
当然,我之所以认定“动物权利”的说法不严谨,还在于谈动物权利不可避免并且似乎根本无法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是:如果动物真的有权利,那么,它的义务是什么?我们显然无法给动物设定什么义务,尤其是无法在尊重动物意愿——如果说权利的赋予可以不尊重相关主体意愿的话,那么义务的设定就显然应当在尊重主体意愿的前提下为其设定某些义务。正如康德曾明确指出的,不可能也不应该存在一种只享有权利而不承担义务的主体。因此,先不说承认动物权利必将导致强加一些义务,就算假定动物不在乎这种义务,我们也还是可以问:难道动物就是那种例外的可以不承担任何义务的权利主体?这显然既不是事实,在逻辑上也有无法解决的矛盾。
那么,是不是本人不赞成对动物的保护?或者说,本人是一个反动物保护主义者?当然不是。本人所意欲表达的基本立场是:
第一,是否要保护动物与是否一定要“赋予”动物以法定的权利其实并没有必然的关系。我们没有赋予自然环境本身以某种权利,但有谁会反对保护环境?或者说,因此就有什么逻辑上的理由导致对环境保护的懈怠?
第二,如果有人(譬如动物保护主义者)出自内心地想要保护动物,那么,除非他能有确切的把握认定动物的本性,否则,轻易地将某种结论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将很可能导致对动物本身的莫大伤害。
第三,如果我们确实想要引起更多数人对动物保护话题的关注,更为可取的方式也许恰恰是抛却某些“虚伪”的高调,而明确地承认动物保护的基点就在于保护人类自己,一如环境保护是为了保护人类自己一样。事实上,这也与人类社会的如下基本经验相吻合:人从本质上具有自私心,因此,最能引起他关注的一定是那些与其利益相关联的东西。
(作者为厦门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sk1188译
什么是权利?
我们对他人权利的认识是基于人所特有的一个性质,即人事有道德感的主体。也就是说,人能够做出道德判断并理解其道德义务。只有人类才能够进行道德判断,并认识到相互之间的权利。因此,权利显然是人类的发明,权利的发展是为了使身处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法律互动关系中的人们能够和平相处,减少摩擦。在人类社会里,那些不能够尽到一个有道德感的主体应尽职责的人,就可能失去其权利。
动物不会作为有道德感的主体去尽到其责任。它们无法认识到其他动物的权利。为了生存,它们本能地杀死并吃掉其他动物。它们的行为是基于条件反射、恐惧、本能和智力的综合作用,但是在行为过程中他们无法进行道德判断。
动物有权利吗?
如果权利仅存在于可以,而且能够相互提出道德要求的的主体身上,那么动物是不能主张权利的。就职于密执安大学和密执安医学院的哲学教授卡尔.科恩在1986年10月出版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中写道:"权利的拥有者必须有能力去理解用于管理所有主体,包括其自身的义务规范。在运用这些规范时,他们必须能够认识到其自身利益可能与正义发生矛盾。只有在一个能够有自控能力,有道德判断能力的群体中,才有可能正确地引入权利的概念。
科恩否定了彼得.辛格和其他动物权利鼓吹者的论断。他们主张,是不是道德主体不能够作为区分人与动物的基本特征,这是因为,有一些人(例如,大脑被严重损伤的人和那些犯了罪的精神病患者)就没有做出道德判断的能力。"用于区分人与动物的那种道德判断能力的高低并不等于对单个的人一个个地试验",科恩解释说:"由于丧失行为能力而不能表现出对普通人来说很自然的道德能力的人当然不能因此被拒绝于道德社会的大门之外。这是一个关于物种问题。"
动物权利哲学漏洞百出
动物利用教育基金会反对动物权利观点,是因为这种观点是把人排除在自然世界之外的一种漏洞百出的哲学。按照动物权利论,一切有感觉的生物--一切能够感知痛苦与欢乐的生物都有权利。
动物权利意味着动物优先
然而,在实践中,这种"众生平等"的哲学却抛弃了平等关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人类。例如,在一个蚂蚁与蚊子和人类享有同等权利的世界里,人为了保护自己免受昆虫的伤害是不能容许的。在《回到伊甸园》一书中,米切尔.福克斯对人类使用杀虫喷雾剂的做法表示愤慨,他声称:"被你杀死的上百万的昆虫中可能只有几只真正会咬人。"
由于接受了这些观点,动物权利运动事实上是在主张动物比人更重要,比人更有价值,比人更需要关爱,既使人的生命受到威胁也在所不惜。动物权利就意味着动物优先。
人类是地球上的二等公民
《读者文摘》专职撰稿人、全国公认的环保问题权威罗伯特.贝蒂罗托1992年在东北地区渔业与野生动物管理局的演说中指出:"当人和人的价值受到自然界诸多食肉动物威胁时,如果严格按动物权利的规矩办,就得禁止对人的直接保护。人受到损失是可以接受的……但动物受损失却万万不能。按照这种逻辑,海狸有权改变洋流,而人却没有这种权利。蝗虫有权大面积的剥夺植物的生命,而人却没有这种权利。美洲狮可以吃绵羊和鸡,而人却不能。"
组成生态系统的各要素之间存在着“物物相关律”和“相生相克律”两大基本规律。“物物相关律”是指自然界中各组成要素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依存关系,改变其中的任何一个事物必然会对其他事物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相生相克律”即在生态系统中,每一生物都占据一定的位置,具有特定的作用,它们相互依赖,彼此制约,协同进化。[1]因而为维护生态平衡,不能任意在某生态系统引进某一物种,也不能任意灭绝某一物种否则两者都会引起生态失衡。
为此,《世界自然宪章》指出“每种生命形式都是独特的,无论对人类的价值如何都应得到尊重,为承认其他有机体的存在价值,人类必须受行为道德准则的约束,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生态伦理关系的两大主张
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分别是“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利益至上主义”这两种生态伦理关系的主张。
(一)“人类中心主义”
1.基本内涵。随着“上帝中心论”哲学思想的瓦解,人逐渐从神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加之蒸汽机革命,使生产力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人类自信心增强的同时追求主体精神的野心空前膨胀。反映在哲学思想上,人类认为自己是万事万物的主宰,人类可以随意的剥削和掠夺自然,自然是为了人类的利益而存在的,即"人类中心主义"。2.理论依据。首先,“每个人都有权取得自己所需要的一切”,人类与动物的关系,被视为财产占有的关系,任何人都有权为了自身利益占有、使用、处置这份财产。其次,“理性人”的法律标准:人类之所以拥有权利,因为人类有理性,有意识,有社会性。因为人类满足这三项标准,在拥有权利的同时,才能承担义务。动物没有理性、意识和社会性,因而不能承担义务,没有无义务的权利,因此动物不能成为权利主体。[4]第三,功利主义伦理观认为:维护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是自然界生命中最大的善,人类作为自然界的成员,理应把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作为最大的善,此外人类相较动物而言,要承担更多的义务,因此人类理应有凌驾于动物之上的权利。[5]第四,权利主体范围的要求权利主体从男人扩大到妇女和儿童,从白人扩大到黄色及黑色人种后还未扩展到无意识的动物种群。因此动物不是权利主体。3.人类中心主义的弊端。正是在“人类中心主义”将人类从神性中解放出来,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然而,以人类为中心主体地位的膨胀,人类肆意的掠夺剥削自然,使大自然一次又一次遭受人类的涂炭。
(二)“生态利益至上”
“生态利益至上”的主要观点是:人类只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人类是自然生态系统这个大网中的一个点,人与自然界的其他动植物没有质的差别,只是发展阶段不同而已;因此,不仅人是价值主体,其他生物也应成为价值主体,当人类与其它物种种群的利益相冲突时,人类应服从生态利益至上。“生态利益至上”承认了动物的价值,认识到了缓解人类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性,但却走上另一个极端。“生态利益至上”认为:当东北虎要吃人时,应当保护东北虎的生存权。因为东北虎属于珍惜濒危保护动物。所以,个人和东北虎这个种群相比,东北虎种群的价值高于人类的价值,东北虎种群的善大于个人的善,应该维护东北虎而不是个人的生存权。
三、“人类和动物为价值主体”的理论观点
由于“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利益至上”两个理论的极端性,笔者主张,在动物与人类的关系上,应该采用“人类和动物为价值主体”的观点,此观点似乎有些中庸之道,但是这是对人类健康权和动物生存权共同保护的一个良策。其核心内容是:承认动物也应该成为道德共同体关心的对象,是价值主体,拥有权利;但是当动物生存权与人类生存权及其他权利发生冲突时,要以有利于人类发展,生态环境和谐运行为处理的原则。
~~~~~~~~~~~~~~~~~~~~~~~~~
读了之后有一些疑问。首先,坚持赋予所有动物与人类平等的权利,这不现实,相信持这种观念的人也是极其少数。至少在中国,大多人关注的只是与人类亲近的动物 - 比如 猫狗等伴侣动物 和 家畜 - 的权利。它们基本上已脱离自然生态,与人类社会紧密联系。在此不禁质疑,在这种背景下的动物权利 真的是一个道德问题吗?我觉得这其实是个情感问题。伴侣动物和家畜脱离了自然,与人亲密而有许多情感联系,所以人看见它们受虐甚至被杀时会有一种同理心(这种同理心的真假或者实质暂时按下不表),觉得悲伤、害怕、可耻。这种情感反映甚至能解释广义上的动物权利。我们是否能做这样的猜想:只是因为动物与人相近,所以人们才声讨动物权利, - 而不是植物权利或者微生物权利。不过这种客观存在的情感需要不应当被忽视。这是一种正常的心理需求。当然 如何满足这种需求就是另一回事了。
动物权利
摘 要:一些学者认为动物跟我们人类一样,可以感知痛苦,并拥有情感。所以它们应该拥有获得尊重对待的平等权利。所以,人类对动物的任何利用方式都是错误的,要求人类完全废除对动物的利用。本人认为,这种激进的完全废除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动物权利违背了绝大多数人类的利益,所以动物没有权利。本文通过实例,论述动物并不具有权利这一现实,同时正确看待动物在自然界中的重要地位,我们应该看到动物保护有利于促进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一面。 关键词:动物权利、道德、权利
一、动物权利的概念
为了提高人类的知识水平,在合理地尊重动物的安乐和符合人道主义精神的前提下,大多数人都承认动物实验的必要性,但是,一个不同的声音和一个逐渐增大的少数派极端分子团体则要求完全放弃为人类目的的,包括实验目的的动物使用,这些人赞成所谓的动物权利这样一种哲学观念。从这一思维方式出发,他们认为动物具有与人类一样的法律和道德权利。 二、动物权利的观点
汤哲学家姆·雷根认为动物天生拥有权利,老鼠和鸡都拥有子午,就像人拥有道德自我一样,他们有资格获得道德尊重,就像人有资格获得道德尊重一样。任何人以任何借口侵犯它们权利的行为都是不道德的,包括吃肉和把动物用于医学研究等。
相反,卡尔·科亨教授则认为,动物并没有权利,但这并不代表我们没有善待或者以仁慈的方式对待它们的义务,但是这种义务并不是来自它们的权利,而是来自这样两个事实,即它们能够感受痛苦,而我们负有避免导致不必要的痛苦或死亡的一般义务。这种义务来源于人作为道德代理人所具有的尊严。
本人赞同动物并不具有权利这一观点。之所以人们认为动物会拥有权利这一观点,一般因为他们混淆了动物道德状况和人的道德状况,然后把仅仅能够正确运用于人的那些概念和原则运用于动物。罗纳德·罗林认为:活着就拥有这利益,生命权,除非是自卫否则无权杀害。赛庞提斯认为:拥有利益,有感觉,就有权利。如果人作为实验对象就必须征得同意,那么动物也是个体,也必须征得他们的同意。但是我们能从动物有利益、有感觉这一事实合理地推导出动物有权利,动物和人类一样拥有道德自主性吗?
下面,本人将通过几方面来论述为什么动物不具有权利这一说法。 第一,如果动物具有权利,那么它们应该具有哪些权利呢?生命的两大基本
需求是生存和繁衍,在这里人和动物是一致的,那么参考人权的内容:生命权、婚恋自由权、财产权、人身自由权等等,那么转换到动物身上就可以是生存权、个体自由权、免受折磨权等等,一些学者则认为动物还应该拥有免受饥渴的自由、免受疾病,伤害,疼痛的自由、免受痛苦和恐惧的自由、表达天性的自由等等。
那么我们在思考下面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一些医学上的治疗方法是通过在动物身上进行实验才获得的,而治疗的方法可以造福人类,那么你愿意去为了动物的权利而去剥夺人类的医疗权利吗?第二个问题是:如果说动物拥有权利,那么一只老鼠的死亡可以等同于一个人的死亡吗?第三个问题是:吃肉在道德上是不是等同于谋杀?第四个问题是:一个着火的房间里有一个人类小孩和一只狗,这是你恰巧经过,你会选择救那个?第五个问题是:豢养宠物和占有奴役在道德上是不是有相同的意义?显然,认为动物具有权利的观点在这里并不能站得住脚。因为我们人类必然是自私的,所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们人类会在保证自己的利益不受侵害的前提下才会考虑其他事物的利益。所以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肯定会选择造福人类自身,因为它可以满足大多数人的利益。对于第二个问题,就从人类本身而言,一个人的死亡必然不能等同于一只老鼠死亡那么简单,一只老鼠死了就是死了,它不会像一个人死了那样会有安葬和追悼。而第三个问题,吃肉在道德上如果等同于谋杀的话,我们绝大部分人类都是谋杀的凶手,这不是很荒谬吗?第四个问题,毫无疑问你肯定会选择救人类。第五个问题,我们对于宠物投入的情感要比其他家禽什么的要多的多,那对于家禽的豢养算是占有奴役的话,我们对于宠物是否算是爱的占有和奴役?如果动物有权利,那前面所有答案相反,这绝对不会被人们所接受,甚至可以说是反人类的思想了。所以说动物是不可能具有权利的。
第二,从道德的角度来说,动物也不具有权利,只不过我们却对它们负有许多的义务,负有做出仁慈行为的义务。所谓道德,也是我们人类自己的主观意识的呈现,道德的标准也是由我们人类自己定的,道德只存在于我们人类世界中,当我们的认知不断成熟时,道德的评判标准也随之改变。
尝试这样一个思想实验:在广阔的非洲大草原上,一直年幼的瞪羚羊,在母亲不小心离开的瞬间被一直猎豹抓住,咬断了它的喉咙,拖入了的远处的丛林中。你会作何感想?如果我们有能力保护的话,我们会去阻止吗?在试想,这时把瞪羚羊换做成一个人类小孩,我们又会怎么做?我们要如何去解释这两者之间的道德差别?毫无疑问,我们会对受威胁的人拥有更大的同情心,同时我们还承认(有意识或者潜意识的),小瞪羚羊的道德地位和婴儿的道德地位有着深刻的差别。在道德世界中,权利是很重要的,但必须予以认真对待,但是瞪羚羊、猎豹和其他的动物都不生活在人类道德的世界中,对它们而言,不存在道德上的对错之分。
我们再来设想一下这样一个场景:某天你在开车去上班的途中,路中突然冲出来了一只小狗,刹车已然来不及,撞上它已不可避免,当你听到车底发出的撞击声,你咬紧牙齿,你很难过,但你的内心在对自己说,如果小狗被撞死的话,希望它没有遭受太大的痛苦,你可能仍然会驾车前行。这时候,假设那不是一只小狗,而是一个刚刚学步的小孩,因为父母不注意,走到了路中,你在恐惧中急转弯,小孩被严重的撞伤,害怕、恐惧向你袭来,一般情况下你肯定会停下来,做你能做的事,赶紧抱起它去医院,联系家人,请求他们的谅解,做出赔偿,以后你还会去医院探望他,给他带礼物等等。那么为什么两种情况下你的反应会如此之大呢?因为这些都源于你对两者的不同道德地位的直觉理解,源于你认识到,小孩拥有全世界范围内你都不能去侵犯的权利,而另一个(尽管有感觉,或许还招人喜欢)却不拥有这权利。
人类有采取仁慈行为的权利,但是利用动物以促进人的福祉研究,并没有侵犯它们的权利,因为动物没有权利,权利不适用于它们。
第三,权利与义务是相统一的,人类拥有着很多的权利,但同时也承担着很多的义务。那么如果动物具有权利,与之所匹配的义务是什么呢?我们人类确实对动物负有很多的义务,但是这种义务是从动物拥有权利这一前提产生出来的吗?否认动物权利的实在性并不意味着否认我们对动物的义务。并不是所有的义务都来源于别人的权利。权利和义务之间的关系不是堆成的。即时权利这一概念不可能适用于动物,但我们对它们也负有做出仁慈行为的义务。所以说动物不可能成为权利的拥有者,因为权利这一概念在本质上属于人,它根植于人的道德世界,且仅在人的世界里才发挥效力和适用性。
第四,对于动物本身而言,认知能力、交流和推理能力都不是问题所在,情绪的能力、偏好和记忆的差别也不是问题所在,即时它们有这些能力,它们也不可能以道德的方式去行动或成为道德共同体的成员。人类群落和动物群落生活的相似性并不能成为物种之间道德平等的基础。一个能遵循真正的道德判断的存在必须要能够理解行为的原理,也必须有能力理解道德论证中的伦理前提的普遍性。
动物权利论所犯的根本错误是,把一个某种环境中非常有意义的概念(道德权利概念)运用到了另一个在其中这一概念毫无意义的环境中。 三、总结
事实证明,动物并不生活在人类的道德世界中,权利根植于人的道德世界中,仅在人的世界才能发挥作用,所以动物并不具备权利。我们不应该混淆动物道德状况和人的道德状况,然后把仅仅能够正确运用于人的那些概念和原则运用于动物。
我的那篇《动物也有权利?》的文章发表之后,不少博友就此发表了看法。我大致看了一下,发现其中认为“动物应该拥有权利”的竟然占的大多数!对此,我在叹服大家对动物高尚同情心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忧虑。因为“动物拥有权利”的命题绝对不像“动物应当受到法律保护”那么简单,一旦“动物拥有权利”得到法律确认,动物就不再是人们的财产,而是和人一样成为法律的主体,我们也将可能遭遇以下尴尬:
1、我们应当杀一只虎还是杀一个人?也就是动物的权利与人的权利谁优先?举个简单的例子,当人们发现一只野生东北虎在猎食一个人时,我们是应该为了救人杀死东北虎呢,还是任由东北虎吃人呢?我想多数人会选择杀死东北虎救人。但大家要知道,如果法律承认了动物权利,这个问题就没有那么简单了。因为作为一个濒临灭绝的物种,一只东北虎的价值绝对不小于一个普通人的价值,至少二者价值应该是等同的,双方的生存权利也是相当地,我们是不是应当冒着让一个物种灭绝的风险去救一个世界上最不缺乏的物种的成员——“人”呢?
2、动物能坐到法庭上吗?也就是动物如何实现权利?大家都知道,动物没有人类如此发达的意识,因此也不可能有权利观念,即使动物权利成立,那也是人类赋予它们的。问题是,当它们的权利受到侵害时,由谁来维护它们的权利呢?没有办法,动物不会说话,因此也不可能坐到法庭上,最终它们的权利还只能是由我们人类来维护。这时我们面临的尴尬时,谁能真正了解动物的真正需要?谁能代表动物提出诉讼?如果说宠物可以由主人代理提出诉讼的话,那么那些种类繁多、数量庞大的野生动物由谁来代表?最要命的是,无论什么法庭,法官和律师都肯定是人,这种人类的法庭能真正保障动物的权利吗?
3、我打了你的狗,我究竟侵犯了谁的权利?也就是说狗是人的财产还是权利主体?例如,我邻居家的狗在我路过他家门前时想过来咬我,我就拣起砖头把它一条腿打瘸了。在现有法律体系下,我的邻居如果到法院告我,肯定会说我侵犯的是他的财产权,因为狗是他的财产。但是,如果动物权利成立,他这个理由就不充分了,因为我侵害的是动物,而不是我的邻居本人,他只能以“狗的名义”提起对我的诉讼。大家听起来是不是觉得有些滑稽?但如果法律承认了动物的权利,这种状况的确会大量发生。
4、一只宠物狗,一只跳蚤,我们凭什么厚此薄彼?也就是我们是不是应当对所有动物种类实施平等保护?我想当我说“宠物狗应该有生存权”时,大家大多没什么疑问,但如果我说“跳蚤也有生存权”时,很多人会说我是疯子。但事实是,跳蚤和宠物狗一样是自然界的动物,跳蚤在世界上存在的历史恐怕比宠物狗要久远的多,我们人类凭什么就因为喜欢宠物狗就规定它们有权利,因为讨厌跳蚤就排除它们的权利,将它们赶尽杀绝呢?这是典型的“物种歧视主义”。事实证明,人们所竭力保护的自然物种,绝大多数都是对人类有益的、与人类亲近的、能够给人类带来精神或物质享受的物种,而一些对人类无关紧要的或对人类有害的物种显然大都被动物权利论者们无情的抛弃了!
5、我们还能吃什么?也就是说如果动物有权利那我们人类还能吃什么呢?我想我们每个人都经常会吃到肉,而且是各种各样的动物的肉,除了什么猪肉、狗肉、牛肉、鱼肉、羊肉等家养的动物的肉外,还有蛇肉、大雁肉、穿山甲肉、野鸡肉等野生动物的肉。当我们从网上看到有人杀死一只猫时我们都觉得太残忍,那当我们每天吃这么多的动物的肉时我们真正感到过残忍吗?没有。因为动物吃草,我们吃动物,这让我们觉得天经地义。如果动物有了权利,人类应该吃什么,怎么吃,恐怕都是问题。
6、我杀一只鹿是犯罪,那我砍一棵树算不算犯罪?也就是说我们承认了动物的权利,那么植物等其它自然物是不是应该也有权利?的确,与动物相比,植物更加缺乏意识,与人类的关系更加疏远。但是,植物与动物一样也是生命,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君不见含羞草也可以在你向它伸出手时“犹抱琵琶半遮面”吗?当看到悬崖峭壁上傲然挺立的松树时你是不是也慨叹过生命力的强大呢?既然如此,我们又凭什么只认为动物有权利而植物没有呢?
为了避免文章过长,今天就简单列举这些。我最终想说的还是,大家不要认为“动物拥有权利”仅仅象“动物应该受到法律保护”那样简单,因为前者意味着在动物面前人类是被动的,而后者意味着人类的主动。当然,不考虑可操作性的因素,前者比后者的保护要彻底的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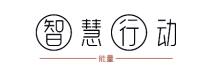
 动物能够拥有权利吗.pdf
动物能够拥有权利吗.pdf